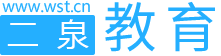“高校师生关系”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中国自古便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如今,“良师益友”也成为主流倡导的师生相处模式。同时,也有一些博士生称呼导师为“老板”,隐含着一种雇佣的关系。每对师生都有自己理想中的相处方式。当师生关系成为一个超出个人层面的社会议题时,有人以感性呼吁师德与相互尊重,也有人呼吁制度上的完善、细化对师生权责的规定。针对“师生关系”这一话题,我们采访了清华的学生和导师,听他们分享自己的故事和观点。
1
学生自述:“换导师”成为一场漫长拉锯战,我的权利谁来维护?
张川 男 25岁 清华大学某工科院系在读博士生
每年开学,我和自己的导师都会进行一次“谈判”。
他找到我说:“我这门课要5个人选才可以开课,目前人不够,你愿不愿意来听?”这个时候我就会问:“您能否答应我换一位别的导师?”
他说:不行。
那没什么好谈的了,我们不欢而散。
这样的场景反反复复,出现了好几次。从2013年开始,我就想要换掉自己的导师,换导师的拉锯战也持续了近4年。
2012年秋天,大四,那段时间我确定了毕业设计的导师。我时常能记起毕业期间,导师让我把自己的论文打印出来,他用铅笔在上面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十分认真负责。最终我申请博士生期间也师从这位导师。
2013年,作为国防生的我确定了未来的就业方向,需要在部队工作两年再回来读研。因为就业方向与导师的研究方向不一致,我提出换导师,当时导师口头上同意了。那时候,他还带两个硕士,由于他的研究方向偏向于传统学科,日渐冷门,那两个学生也想换导师。导师告诉我:“你们不能同时换,否则我就没学生了,等你回来再换吧,先缓两年,稳定一下民心。”
两年后,我返回学校,导师却不同意我更换,原因是,那两个硕士已经毕业了,他就又没学生了。于是就有了开头的对话。既然原导师不同意更换,我只好求助于其他的帮助。
为了更换导师我前后付出了不少努力。我翻阅了研究生手册,上面有一页写着《清华大学研究生调换指导教师管理暂行办法》,这个管理办法是2012年11月27日研究生院院务会讨论通过的。我认为自己符合办法中所说的”特殊情况”(导师由于退休、离职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指导;院系或导师认为必要),可以申请更换导师。
我拿着手册去找过研究生院,找过学院的教务,甚至给校长信箱写过信。
最终,学院行政会议讨论决定同意我更换导师。
然而,直到今天我的换导师之路也没有走向成功。虽然事实上,我已经参与新的导师组里工作了,也不再去原导师那里打卡,但因为原导师不同意更换,所以名义上我还是他的学生。也没有人可以替我说话。这样翻来覆去地“折腾”了几次,我对换导师的态度也变得冷淡,无论如何,我作为学生都是弱势的一方。而我们学院大部分导师,真正用于指导学生的时间并没有多少。
以我现在的导师为例,他也主要是把学生当作一个劳动力,我们很多人在背后也管老师叫“老板”。老师说得很明确:毕业论文是你自己的事情,在我这,你必须得干够活儿。如果有学生想离开他的组,他也会说:“你要换导师可以,但你得把我的项目干完。”相比于之前的导师迟迟不肯放人,现在导师的“利益诉求”就很明确。
事实上,我周围也有一些更换过导师的同学,我们可能代表了部分工科院系的特殊情况。大部分情况下,导师与学生的关系要看师生的追求是否一致。
对于基础学科来说,学生和老师的诉求都是发文章,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不容易产生矛盾。
但对于我所在的院系或其它传统工科院系,导师的考核指标,除了发文章就是承接项目的金额。由于我所在的方向发文章比较困难,所以做项目就是老师的主要需求了,而这跟我要毕业的需求就不一致了。所以很容易出现问题。
但不管怎样,我认为,在师生关系中,学生的力量太小了,以至于不能平衡。我的同学在和导师发生矛盾时,导师一句“你能不能毕业我一句话说了算”就让他无话可说。在导师负责制下,学生的发文章、转导师、退学全部需要原导师的同意,原导师的“人品”就显得非常重要。网上有研究生们开发的“导师评价网”,在上面可以匿名了解某些导师的情况。导师的“人品”、“师德”超越了学术水平,成为学生最关心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这背后就是权力不对等的一种体现。
导师自述:导师的职业道德很重要,但制度约束也不能缺失
02
王程韡 男 35岁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0年的时候我拿到了自己的博士学位。2016年,我正式成为博士生导师,招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学生,目前他也已经毕业了。从博士毕业到成为导师,中间只经过了6年,这在以往的制度中是不可想的。这要追溯到2011年清华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制度改革:学校取消博导评聘制度,教师系列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和Tenure Track系列的教师,均有招收、指导博士生资格。导师不再需要经过“讲师、副教授、教授”的上升通道,经过审核便可以直接成为导师,把一线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我也算是改革的受益者。
一个教师想成为博士生导师,首先需要有一定的学术能力,其次需要有项目的资金、经费。从我成为博士生导师的过程来看,对于教育能力和师德方面的审核几乎没有。我们在成为导师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一些有经验的博士生导师会给我们作报告,但是没有对讲座内容设置考核。
我至今都记得培训中一位前辈说:“你一定要像去找一个男女朋友那样去找你的学生,因为这是一个长时间的承诺,很容易因为性格等因素相处不融洽。”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个比喻有点“政治不正确”,但无疑他的形容很贴切。
在成为导师前,我很认真地回忆了自己在求学过程当中遇到的那些让我真正很感激的前辈,从自己的求学过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第一位就是顾淑林老师,她开过一门课叫《创新经济学》,特别热心地帮助年轻人。第二位是我在哥大访学期间的导师Richard R. Nelson,他在学术上很有造诣,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式;他做过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还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访问期间,每周都会和我meeting,讨论我关心的内容。每周一我把要讨论的内容发给他,然后周三我们在一起讨论。他还会把办公室借给我用,要知道,在哥大,办公室是一个非常紧缺的资源。就是这些前辈,让我知道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导师。
当我成为导师后,我会带着自己的学生读文献。因为很多文科类的博士生其实并不知道怎么读书,我想先帮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可能有学术成果的方向,让他们阅读。作为人类学研究者,我们做的很多工作都是理解别人,理解社会边缘群体,我也会尽可能去理解自己的学生。而我挺欣慰的一点是,当我对学生很严厉的时候,他们也能理解我,也都知道我是对他们好。
而这些都并非“导师手册”要求我做的,是出自每个导师的自觉。事实上,我们对于导师的监督和权责划分是不够的。我也时常反思中国目前的导师制度,它很像是西方的导师制和中国的学徒制中间的产物。而且,中间有许多笔糊涂账。国外的普遍状况是,如果你的博士读得不好,很有可能会被退学。但在中国,退学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我们也很少听到有人退学。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学生退学了,导师如何证明自己对学生尽到了指导的责任。甚至很多导师,对学生都是“散养型”的。
我在曾经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有一个短暂的访问,那个学校的规定是,导师跟学生meeting要有当场的录音录像,这其实是一个保证师生定期的学术沟通和防范性骚扰非常好的办法,对学生和导师双方的权利都有保障。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导师指导方面的规定不够细化,甚至是缺失。
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的是,在师生关系中,学生的确是出于劣势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会和学代会可以挥发一定的作用,代表学生的权益。涉及到学生利益的决定,应该有学生的声音。但制度的变革涉及到多方的利益,所以很难在短期之内发生变化。
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我首先要对自己有所要求,要警惕有一天自己成为自己曾经讨厌的那种人。所以要想办法去充实自己,这个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