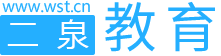1838年,一所叫布朗学塾(Brown School)的学校在北加利福尼亚州成立。
在19世纪90年代,布朗学塾几经风雨早已更名为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大商贾华盛顿·杜克(Washington Duke)先后为这所学校累计捐款近40万美元,而让华盛顿的印记更深刻镌刻在圣三一学院历史中的还有他确立的学校向女性开放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
在1924年,华盛顿之子詹姆斯·杜克(James B. Duke)利用4000万信托建立了杜克捐赠基金,在学校校长的坚持下,詹姆斯最终接受了将学校更名为杜克大学以纪念其父亲的建议。在接下来的3年里,整个校园进行了重建,同时还开办了神学院和研究生院,杜克大学由是正式成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杜克大学已经成为现在美国最声名卓著的高等学府之一,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 World Report)》发布的2019年美国最佳大学排名中,杜克大学名列全美第8。
更名杜克大学90年后,在中国的昆山市,这所学校与当地政府以及武汉大学合办的大学成立了,名曰昆山杜克大学。无论外面世界如何喧嚣,这所学校已经默默地将自己楔入了这座县级市未来的发展轨道里,而这条轨迹也探索了国家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同样不言而喻的是,这所学校、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大洋彼岸的美利坚息息相关。
昆山杜克大学迎来第一批来自全球的本科生
应运而生的大学
昆山,西邻阳澄湖,左近长江出海口,以中国区域行政级别划分,它只是苏州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像昆山这样的县级市约有370个。以距离论,昆山距离苏州大约只有30公里,距离无锡约摸有70公里,而距离浦东则堪堪超过100公里而已。以历史沿革而论,直到1989年,国务院才批准其撤县建市,而直到2011年,昆山才被列入江苏省省直管县市试点。
普通的县城总是相似的,而不一般的县城则有着各自的不一般。
昆山不一般的地方在于,自2004年以来,它就一直牢牢占据着中国百强县第一的位置。在2017年,它的生产总值达到了3520.35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同年宁夏全省的生产总值。
但在很多年前,情况还不是这样。
在改革开放之前,昆山是苏州市下辖六县中的“小六子”,直到80年代中期自主创办工业开发区以招徕“军转民”的军工企业和从上海迁出的工业企业,昆山快速崛起。
昆山离上海近,进出口都方便。早期的台商曾经如此评价昆山的优势条件,与此同时,比上海更高的行政效率和更诚恳的招商引资态度帮助昆山成功吸引了大量台商投资建厂。
随着从农业向工业转型、内销经济模式转向出口导向型经济以及金融危机之后的企业资源从分散从集聚形式的转变,自80年代到21世纪初,经济发展狂飙突进的昆山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逐步实现了其富足持续发展的基础。
在2008年时,昆山人均 GDP 达到了120882元,根据霍利斯?钱纳里(H.B.Chenexy)的工业化阶段来划分的话,则这座县城此时便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实现后的发达经济阶段。
但是,与蓬勃增长的经济总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下的质量。
2006年昆山全部 IT 产业研发支出为25.05亿元人民币,在 IT 企业销售收入中的比重仅有1.71%,全年笔记本电脑产量超过2500万台,然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器数量则是少之又少。
研发能力和投入匮乏的源头自然是人才的不足,到2008年时,昆山人才数量超过16万,其中大专和本科学历人员在其中的比重分别为52.08%和45%,而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的比例仅仅只有1.2%。
昆山终于意识到,一个没有科研基础设施和氛围的小县城终究是是无法吸引到足够的科研人才的,遑论技术研究和企业、市场应用之间的相互转化。
这座县城此时已经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产业结构由低到高的升级阶段,然而,科研实力和资源成了它最大的掣肘。
在这种背景下,昆山杜克大学应运而生。
大学带来的连锁反应
“我们不能急功近利地去办一个大学,办很短的几年,就期望它能够带给我们多少多少。”副市长李晖在去年年底才走马上任,她告诉我昆山对合办大学的期许。
发展崛起至今不过30多年的昆山在教育基础设施方面显然无法和相邻的上海相提并论,更不用说在外人的第一印象里,尽管是百强县之首,但它也终究只是一个县城而已。早先,昆山便已经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短板,于是邀请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科院及浙江大学等院校在当地合作开办创新研究院,利用高校资源结合昆山本地的产业资源来更好地实现产学研的转化。
现任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90年代中期就创建了 OLED 项目组并成立了中国大陆最早拥有 OLED 产品生产能力的维信诺公司,2008年在昆山建成了大陆第一条 OLED 大规模生产线,到2017年时,维信诺以38.9%的占有率成为大陆出货面积最多的面板厂商。
这是昆山将学校资源、技术研究和企业生产结合得最成功的案例之一,谈起邱勇校长和维信诺,李晖副市长赞许道。事实证明,占尽天时地利的昆山一旦获得一流的人才将会爆发出较之单纯招商引资更为剧烈的能量。
在寻求第四次经济和产业转型机会的关键时刻,昆山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能在当地拥有一所自己的一流大学,吸引和培养更多的一流人才,才能将产学研环节真正闭合起来,而这正是昆山新转型的关键。
“现在的大学,不再是脱离社区或脱离社会的学术孤岛,大学越来越希望对所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我们的教授们非常积极地参与本地和国际研究项目。从当地经济需求和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贡献能解决具体问题,而且可以发挥巨大作用。”昆山杜克大学现任常务副校长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曾经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他深知,唯有立足本地,这所合办大学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数年前,他曾经担任大连市长夏德仁的科技顾问,当时,英特尔公司计划在中国投资创办半导体厂,这个被英特尔称作“海神计划”秘密计划寻访了若干中国城市,最终,大连在挑剔的英特尔公司投资评估中拿到了最高的分数。
西蒙副校长回忆道,大连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不小的优势,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便是大连理工大学坐落其中,而这所大学培养的人才和拥有的研究资源恰恰最符合英特尔亟需的半导体研发生产需求。
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在今天,这一判断不仅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贬损,反而越发显示出其高瞻远瞩。
一座一流大学足以改变一座城市。
昆山杜克大学还是一所年轻的大学,甚至直到2018年才开始正式招收第一批本科生,但李晖副市长已经对这所大学的未来充满期待,借助杜克大学的平台和资源,作为一个县级市,昆山吸引到了更多的一流人才,而这又能更好地帮助当地的企业进行技术升级,依靠研究资源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集聚效应,昆山又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来撬动当地个产业升级转型的杠杆。
“原来我们觉得谈一下很简单的,你做什么,你投资多少,你要多少地,你能产生多少的工业产值贡献多少税收。现在我们更多看的是团队,首先看你在行业里面处于什么地位,再看你是有什么专家团队来支撑你。”李晖副市长惊喜地发现,昆山杜克大学的建立甚至已经改变了他们招商引资的思路,之前对这所学校的憧憬逐渐在现实中实现。
注意到这些变化的不止是昆山市而已。
昆山杜克大学校区
“昆山杜克大学的课程设置是跨学科的,科研团队也不是以传统的院系为基础来搭建。大数据和智能的未来不是纯技术流,而是要将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应用到各个传统行业。”昆山杜克大学应用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以及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李昕总结道。
李昕教授不仅仅是 IEEE 会士,他本身就是一位创业者,早在2005年就与人合伙创办了 Xigmix 公司,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应用。兼具业界和学界经验的李昕教授对产学研的关系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告诉我,从学校到公司再到市场之间的险阻远超人们的想象。
未来传统制造业升级转型的方向就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工业自动化和研究应用将会迎来爆发式地增长,富士康集团一直与李昕教授合作进行制造业大数据分析。比起跨区跨洋合作,一所本地的一流大学和相关专业的一流团队及研究资源无疑更能满足企业的意愿。
“我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鸭是最知道这个水暖的,所以我想企业对市场是最敏感的。”李晖副市长则这样告诉我。
在人工智能和制造业领域,包括 Google、Facebook 以及国内 BAT 这样的公司虽然在人工智能算法研究上游刃有余,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制造业经验,于是,技术往往难以落地,而恰恰是像富士康这样的传统制造企业的优势,虽然在人工智能的前瞻性研究上并不出类拔萃,但是在实际应用上,这些厂商却往往独领风骚。
在市场还不明晰、商业化前景尚未明朗的局面下,互联网公司的投入相当谨慎,离市场和应用越发遥远,而传统制造企业也不愿轻易把自己的数据拱手相让,于是,在人工智能和制造业结合的领域,互联网公司和传统企业之间渐渐升起一道柔软的铁幕,双方对彼此都有需求,然而,这种意愿越是强烈迫切,其间的阻力和矛盾反而就越大。
大学的资源和立场使得它发挥出一种超乎寻常的作用,扮演起两种企业间的粘合剂和缓冲器的角色。一方面,它能够和互联网公司合作互补进行前瞻研究,而另一方面,处在一个工业集聚效应明显的区域,大学的研究往往更加贴近当地企业的应用需求,在长期研究和以市场商业化为目的的应用研究之间,大学无疑更加灵活,而昆山杜克大学的跨学科优势让它在昆山当地产学研互动中的威力更加突出。
如果以昆山周边的水文条件作譬喻的话,此前,它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聚焦于自身、以自身为单一生态系统中心的阳澄湖模式,那时的昆山是一座依靠招商引资在经济总量上睥睨四方的百强县。
而现在,随着全球化的扩散和昆山杜克大学的建成,它正逐渐嬗变为吸收涵养周边资源同时将自己纳入一个复杂变动的经济和产业体系中的长江模式,只有从源头和根本上保持自我创新和吐纳,大江大河才不会断流,才能奔流到海不复还。
相比静态的湖泊,动态的江河汹涌澎湃,其间不免有落差间或干涸,但太多的历史经验已经不言自明,任何固步自封的系统都必然陷入崩塌,而只有开放活跃保持包容和吸收的系统才会有着恒久的生命力。
昆山杜克大学便是昆山和新的江河发展模式的活力的最重要的来源。
碰撞与融合
“昆山杜克大学是独一无二的创举。这是一所国际大学,它不仅仅是一个中美机构,而是希望成为一个全球性高校。这是昆山杜克大学非常重要的优势。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重新思考课程设置、学术项目以及研究项目的巨大机会,不必像其他高校一样顾虑传统,仅能在既定的框架内行事。”杜克大学第10任校长文森特·普莱斯(Vincent Price)说。
杜克大学教授格里高利(Gregory C. Gray)教授对猪和猪的遗传组成非常感兴趣,曾经帮助中国同行们在2014年组织了第一届同一健康(One Health)国际研讨会。这名国际知名的流传病研究专家来自北卡罗莱那州,这是美国著名的养猪大州,而中国同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市场之一,于是,格里高利教授也顺理成章地来到了昆山杜克大学进行研究。
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李彬彬团队通过 GPS 项圈定位追踪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变化情况
李彬彬教授早在杜克大学读博士期间,就尝试利用技术手段通过足迹识别来追踪大熊猫个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这些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应用,为她的野外大熊猫研究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她告诉钛媒体,研究团队在野外已经铺设了很多红外相机并拍摄了大量照片,但是对这些图像数据的识别和处理在过去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大部分依然需要人工识别,而图像识别技术的成熟将极大地解放人工投入。对于有大量数据积累的物种,图像识别更稳定,也将会在精度和准度上超过过往人工作业的结果。
显然,生态保护早已经不再是一门单纯的学科。
李彬彬教授认为,相比国内的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在科研上的一大特色便在于打破了传统的学院科系堡垒,于是,有着不同学术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们可以共事研究同一议题。李彬彬教授自己专长于保护生物学,而那些研究经济学与政策分析的研究者们也可以为生态保护里更加现实的问题提供答案。
“许多野外的项目需要不同的技能,有人擅长野外数据收集,有人擅长做统计模型来统计和分析,还有些人可能对经济更感兴趣,那么就可以做社区的工作。这个行业非常综合,只要你想做,那么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技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李彬彬教授这样总结,从去年7月开始,她开始在昆山杜克大学担任环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杜克大学地球化学和水质学专业教授兼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教授的阿文勒·梵格西(Avner Vengosh)博士一直关注着中国的能源安全,尤其是四川省的页岩气应用及其开采运输过程中的废水污染问题。在美国,存在着不少因为污染物渗透到土壤里且无法清除的“超级基金场址”(Superfund site)重度污染区,在发展新能源页岩气的同时如何避免重蹈美国覆辙是梵格西博士和昆山杜克大学现在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参与过两次奥运会污染治理与疾病相关性研究的张军锋博士现在是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的教授,该中心主任张俊杰教授如今关注的是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的关系,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只有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才能消除外界的质疑并真正推动中国“一带一路”政策长久持续下去,最终推动中国和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
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发展趋势吸引着无数的研究者和拓荒者,他们或者在这块土地上仔细追寻着40多年来高举振飞的蛛丝马迹,或者试图从中找寻出任何足以成为经验或失败教训的事实,还有更多的人热切地盼望着参与到这一古老国度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去。
在全球化浪潮起起伏伏的今天,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方方面面都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对他者来说,这就是一块充满未解之谜的新大陆,等待着去探索和解答。
昆山杜克大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在第一轮教师招聘中,25个教师岗位总共收到了1300多份求职申请。而在第二轮招聘中,共有超过1400人申请了另外20个教师名额。
“我们不是向中国输入杜克大学技术的管道,那不是我们的目的。坦率地说,昆山杜克大学的目的是创造我们自己的技术,我们自己的新知识。”西蒙副校长说完,扶了扶他的眼镜,年逾六旬的他有着丰富的中国经验。
无论是昆山还是杜克大学清楚地知道,只有把杜克大学的学术资源和昆山本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展开更有针对性的合作,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双方各自的优势。
“传统上说,我们所认为的社区是自己所在的学科群体和我们的学生们。我们很少会想到:我住在昆山,我对本地的居民负有责任。”对于合办大学的意义和作用,昆山杜克大学环境健康助理教授纪思翰这样评价。
昆山的这所中美合办大学的研究思路正在发生改变,在纪思翰教授关注的公共健康领域,他们从研究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的平均值转变为研究本地疾病负担,深入分析本地社区正在发生的疾病以及可能需要采取的政策。
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处在高速发展迅疾变化之中,既有的思维和理念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态势迅速崩塌,如何应对这样复杂混沌的剧变是中国与美国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昆山、杜克大学及 DKU 的机遇。
西蒙副校长始终提醒着中国的同行们和行政长官们,高科技工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行业,永远都在变化之中。
杜克大学所在的北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带在美国与硅谷等齐名,这里聚集了包括杜克大学、北卡州立大学以及包括 IBM、葛兰素史克等在内的大公司。但西蒙副校长告诉我,这些大公司现在都已经大力缩减规模,与中国人熟知和想象中的那个园区大相径庭,现在的北卡三角研究带与以往已经截然不同,旧的模式几近土崩瓦解,而新的高科技园区模式则蔚然成风。在这种模式下,创业企业倾向于选择城市,利用其中成熟的基础设施来快速发展。
“昆山不是要建成一个20世纪高科技园区,而是希望建立一个能适应21世纪新形势的高科技园区。”西蒙副校长一脸严肃地告诉我。
21世纪的新形势是怎样的呢?让我们回到十年前,2008年8月,奥运会在北京举行。
此前数月,北京市采取了包括关闭工厂、限行车辆限行、遮蔽工地等在内的措施来治理备受诟病的空气污染问题。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有了显著改善。
中美合作发布于2015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在奥运会孕期刚好处于第8个月的孕妇生下的婴儿比2007年或2009年同一时期出生婴儿平均出生体重增加了23克。
两国团队另一项历时6年的研究发现,从奥运会前到奥运会期间,健康年轻人的 sCD62P 平均水平下降了34%,vWF水平降低了13.1%,研究人员认为北京奥运期间空气污染物水平与健康年轻人心血管生理学指标的急性改变相关。
颇具黑色幽默效果的是,破坏自然和环境污染的结果最终还是反作用于人们自身,而婴儿和年轻人这两个代表着未来和希望的群体恰恰是其中最显著的受害者。
落后地区及欠发达地区为了振兴经济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仅是欧美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寻求富强的现代中国也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疾驰的足迹。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污染,落后的产业结构形态加剧了环境的恶化,而这样的经济形态又使得人们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进一步恶化,于是,消费、产业调整转型和环境问题构成了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正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指出的那样,当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时,环境退化的程度处于较低水平,随着经济增长加速, 环境就会不断恶化,但当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时,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人们环保意识和技术手段的提升,环境恶化现象就会逐渐减缓,并开始趋于改善。
显而易见,环境问题最终归根到底是一个经济问题,只有真正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利用新技术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这是向着现代化狂奔的中国的愿望,也是执着地寻找着第四次转型之路的昆山的目标,同样还是年轻的昆山杜克大学在全球化和在地化之间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平衡点。
就算风起云涌,哪怕九死一生,伟大的航海家先驱们最终还是证明了世界是平的。
这个世界无法忽视也不可能隔离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同样,一个渴望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也必然和世界市场和体系联系在一起。
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历史和文明的中心不断迁移着,中美两个大国如今在汹涌澎湃的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中竞逐起伏。
事实上,在漫长而倥偬的岁月之中,太平洋两畔的两个超级大国如影随形,一方总是无法摆脱对方的冲击,而另一方也总是欲罢不能地回应着对方。
中国不再是一个面对冲击的失语被动的回应者,她迫切地寻求着表达和成长的机会。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问题即是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问题同样也是中国的问题。
“昆山杜克大学和杜克大学的研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做出贡献,就意味着能够对全球做出多大的贡献。”和绝大多数高等教育工作者一样,纪思翰教授也同样坚信着全球化的力量和它带带给世界的福祉。
昆山、中国与美国、世界,在这所合办大学里最终寻找到了自己最理想最完满的连接方式,而这也恰恰是这个世界维持和谐运作与生命力的根本。